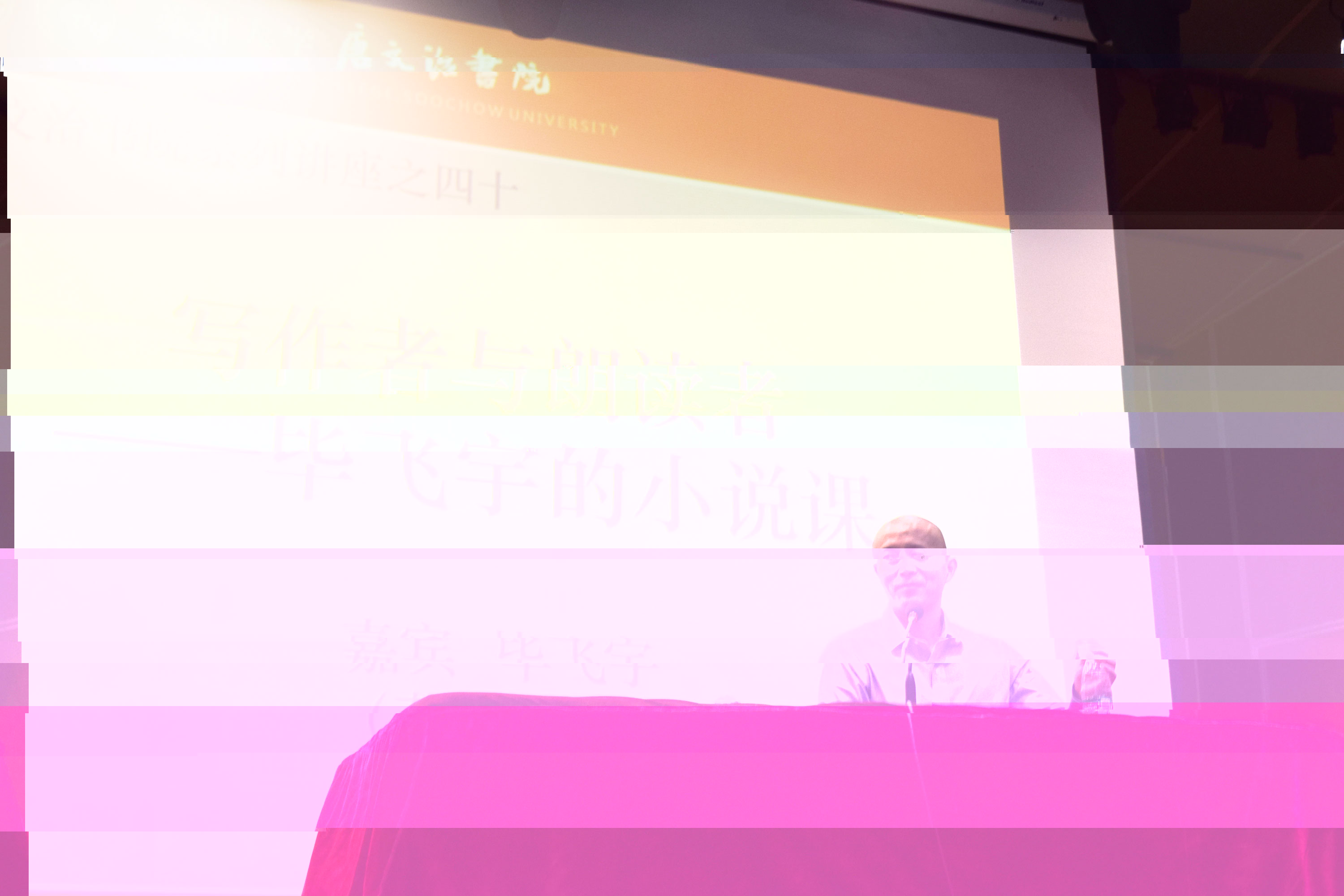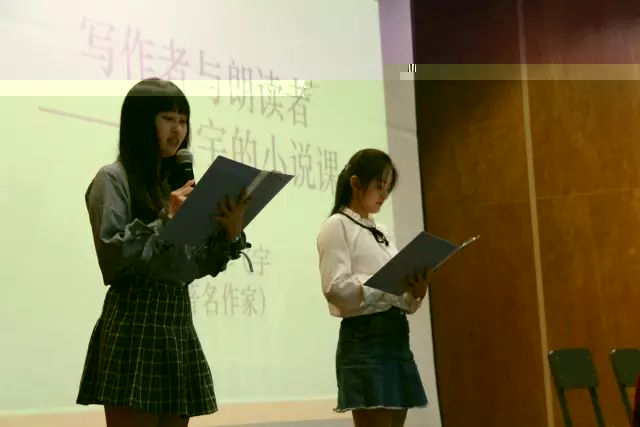bet356系列講座之四十寫作者與朗讀者——畢飛宇的小說課
2017年9月16号晚7點,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南京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著名作家畢飛宇老師應bet356在线官方网站邀約,莅臨bet356在线官方网站,于我校601号樓音樂廳成功開展以“寫作者與朗讀者——畢飛宇的小說課”為題的文學講座。
講座現場極為火爆,早已擠滿了慕名而來、翹首以待的蘇大學子,畢飛宇老師的出場收獲了熱烈的掌聲,文學院王堯教授代表全體師生,對畢飛宇老師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與蘇大學子分享交流表示真摯的感謝,并高度肯定了他為中國文學界所做的貢獻:在90年代打破束縛,建構屬于自己的獨特文學世界,風格鮮明,獨樹一幟;在作品中通過多種視角審視空間,方位多元,創作手法豐富;是受到海内外廣泛關注和喜愛的當代作家之一。 1 演講環節 畢飛宇老師緊扣“寫作者與朗讀者”,與同學暢談自己創作時的心路曆程。他将自己分别定位為“寫作者”和“朗讀者”,先作為純粹的“寫作者”進行創作,再以“朗讀者”的身份反複閱讀修繕自己的作品。其中,畢飛宇老師提及作品也需要有自己的“嗓音”,本着被朗誦的可能性堅持賦予作品以音樂美,從而使小說語言獲得極大的提升。此外更重要的是通過身份的互換完成對作品最重要的“體諒”,通過對人物的感同身受來貼近角色、塑造角色。“寫作者”過度膨脹的自信需要通過他本質的身份,即“朗讀者”來矯正過往,打擊、警醒和提示“寫作者”,通過兩個身份不斷制衡,最終滿足讀者的期望和作者的需要,并使文學作品中的道德性得到循序漸進的升華。 整個講座深入淺出,畢飛宇老師通過與朋友導演婁烨夫婦的問答、童年時期父親對他的讀詩指點、創作短篇《玉秀》時的心路曆程等親身經曆,講述了“寫作者”與“朗讀者”在自身創作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相互制衡的關系。他作為小說家的幽默、敏銳和理性在他的分享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他新奇的角度、獨到的見解、揮灑的語言和親和的态度深深折服了現場的觀衆,令全體師生受益匪淺。 精彩語錄 1、一個人有各種各樣的社會角色,但本質性的身份隻有一個。每一個人在做一件事情時都帶着自己的身份,這是容易被大部分人忽略的事實。 2、我建議你,無論你做什麼,無論你在生活中決定做什麼樣的人,你做好研究一下自己,我究竟是誰?找到那個真正的身份後,無論從事怎樣的工作,過怎樣的生活,都會有所幫助。 3、我沒有成為一個詩人,我成為了一個小說家。于是我就給自己一個要求,如果有人拿我的小說來讀,我希望它讀起來是好聽的。 4、作為作者覺得出彩,作為讀者無法接受,兩個身份相互膠着。“寫作者”過度膨脹的自信,需要通過其具備的本質身份“朗讀者”來矯正過往,打擊、警醒和提示寫作者,兩個身份不斷制衡,最終實現滿足作者的需要和讀者的期望。 2 朗誦環節 在第二環節中,來自bet356的同學們,朗誦了畢飛宇小說作品中的《蘇北少年堂吉诃德》、《青衣》、《推拿》、《玉秀》、《哺乳期的女人》片段。用聲音的方式,将文字展現在大家面前。 3 問答環節 Q1:您的作品中,會有很多兩個角色之間的心理博弈,您在創作的時候會不會非常享受角色轉換的創作過程? A:一定的。寫作的時候,許多時候我自己在和自己博弈,哪怕手上沒有在寫,吃飯散步的時候都很糾結。寫作一定有它的痛感,但問題就在于,我們經常去電影院看電影,經常到戲劇院去看戲,我們聽音樂、看小說,所有和藝術親近的人,都有一個感受,我們接受藝術的時候,不僅僅是享受,有時候是為了那個痛感才去接近藝術。 審美是一個非常怪異的東西,它和肉體的享受有本質的區别,肉體的享受大部分和快感聯系在一起,精神的享受通常是痛感和快感同時存在的,這就是藝術審美的特征。所以作為一個寫作的人,作為一個藝術家,承受痛苦是他的本分、是他的工作。 Q2、一部作品,一個是寫作者一個是朗讀者,可能還有評論者還有翻譯者,評論者對您的寫作有沒有什麼幫助? A:你剛剛分出了幾個身份,讀者、寫作者、評論者、翻譯者。我們能不能把評論者、翻譯者去掉。因為在我眼裡,評論者首先是讀者,翻譯者也是讀者。當你把文學批評家、文學史學家,從讀者中拎出來的時候,對一個作家來說是世俗的。如果作家的心裡隻有讀者,把批評家、文學史學家、評獎的評委、報社的書評人、翻譯家當做讀者,内心會簡單的多,内心會湧起一個服務的欲望。要知道,作家是要為讀者服務的。 Q3、您筆下的青衣筱燕秋和作家畢飛宇之間發生了一種怎樣的關系? A:《玉米》、《玉秀》、《玉秧》和《平原》,它們是和我(作者)的生命有關的,我把我生命裡的經驗、經曆、曆程變成了這幾個小說。但問題是,一個小說家,不僅僅是呈現他的經驗,經曆,思考,情感,他的人生道路。作家也是人,作家也有非常頑皮的時候,作家也有自己和自己鬧變扭的時候,作家也有逞能的時候,他就是要告訴自己,我究竟有多勇敢。《青衣》,寫在1999年,那一年我35歲,不是55歲、也不是65歲,一個35歲的年輕人不年輕,但是也不老,他想做一件事情,就是做自己不可能的事情。35歲的我就是要寫自己想寫的東西,而不是自己能寫的東西。我根本沒有想到我要寫《青衣》,我對京劇一竅不通,在我的人生經曆裡,沒有和任何演員打過交道。有一天晚上我意外的發現一本大學裡買的書《京劇知識一百問》,我一直沒看過,我就看完了這本書,用我僅有的一百塊錢我去了紐約,然後我活着回來了。 Q4:小說擁抱了這麼多可能性,那你的寫作,你希望它能給别人一種指引還是别的什麼(原因)? A:我非常清楚我是一個小說家,不是一個文學老師,我更不是一個人生導師。宗教和文學有一個巨大的區别,宗教在相當大的程度是承載道德,作家不承載道德。起碼對我來講就是這樣。 在作家這裡真正值錢的是對人性的理解,是作家對人性的包容,是作家對人性的無奈,因為這些作家會在對人性的理解、包容、無奈達到最高的道德标準,而不是别人承載的道德。正如雨果所說:“在絕對正确的正義之上,有絕對正确的人道主義。”在我看來,你個人承載着的道德是毫無意義的。真正有價值的寫作是懷着人道主義的寫作。 Q5:我在聽您今天講座的時候想到了西方美學的一個概念“隐含讀者”,您在創作的時候,有把朗讀者畢飛宇放到隐藏讀者裡面嗎?如果沒有,您在創作的時候,您的隐藏讀者是那些人呢? A:福樓拜說過:“作者隐秘”。從福樓拜角度來講是盡可能讓作者隐去,從接受美學來講,讓讀者隐去。毫無疑問,如果這兩方都能成立,這兩個隐去的“合謀”就是非常動人的。但是很難做到。如果選擇其中一個,我甯可選擇福樓拜而不是接受美學。我甯可不讓自己作為“朗讀者”的身份清晰一點,而願意讓自己作為寫作者的身份更隐秘一些。因為從本質上說,我是一個作家。當然我也是一個讀者。 Q6:您覺得“史詩”模式困境最大的問題在哪裡?而結交“小群體”對這個困境有什麼突破? A: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從五四運動開始之後,中國的文學必然是“史詩”文學,因為中國文學運動是伴随着五四運動起來的,五四運動和救亡運動聯系特别緊密。所以當一個文學從業人員剛剛從一個世紀初拿起筆時,他的心中承載着國家與民族的命運。所謂國家與民族的命運,其實就是“史詩”模式。 第二:中國是沒有小說傳統的,五四之後,小說傳統走進中國。俄羅斯和蘇聯文學小說傳統占據中國小說重要比例。五四之後的新文學接受俄羅斯文學,接受更為廣泛的不僅僅是小說文本,還有“别車杜”——“别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别車杜”都是民族主義過程中産生的文化影響。他們美學思想中更多強調的是文學參與社會,文學參與國家的民族進程這一類的文學思想價值。五四以後,尤其是49年之後,中國全面接受蘇聯,一定有它的道理。無論是政治上、無論是經濟上、無論是舞蹈上、無論是音樂上、無論是文學上,都是這樣的模式。在長時間内,雖然我們的文學在和俄羅斯文學、蘇聯文學有很大的區别,但在大體方向,價值取向大體類似。問題在于1979年之後新時期來到。文學開始多元化,所謂文學多元化就是價值觀多元化。所謂價值觀多元化就是一方面有些作家在因循五四的文學價值觀,一些作家在因循俄羅斯蘇聯的作家,一部分作家在因循歐美的作家。歐美作家的價值觀更多是延續着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更多強調的是生命個體,而不是曆史、社會。所以在大的背景下,新的時期文學才可能出現一個新的文學品種——先鋒小說。 (本文轉載自bet356在线官方网站團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