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是不可能的,所以需要研究
2016年12月20日晚六點半,bet356系列講座之三十四在1005-5339準時開場,在講座開始前一小時就有同學在門口等候,可見大家對于此次講座的期待。講座由季進院長緻開場詞,作為老友,季進院長的開場向我們展示了柯雷教授的學術研究涉獵之廣泛,并燃起了大家的興趣。作為一個研究中國當代詩歌的學者,作為漢學研究“局内人”的他對漢學研究又有怎樣的看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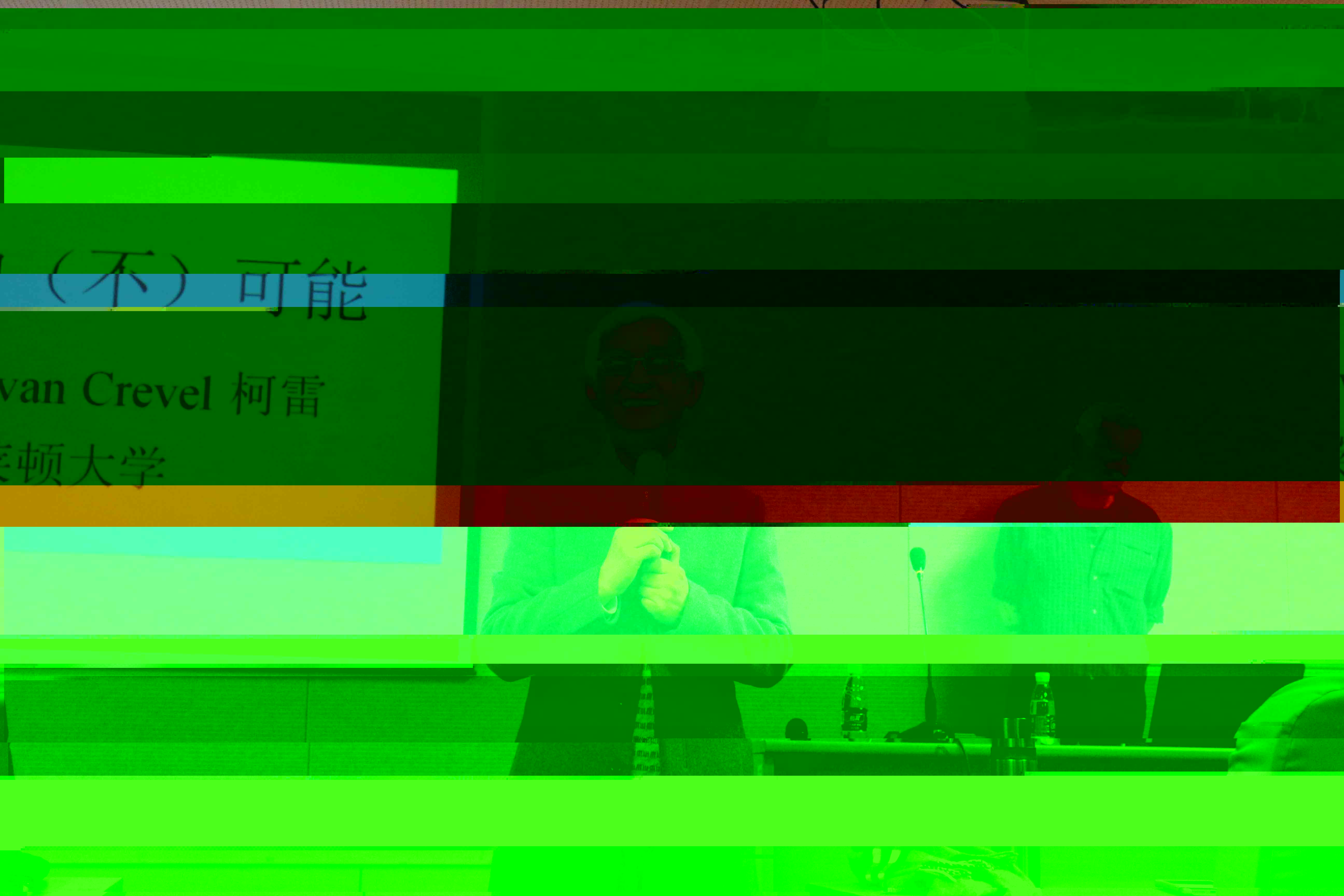
柯雷教授首先向大家介紹了萊頓大學的第一位中國語言文學教授,并且介紹了另外一位現在萊頓大學任教的Jue Wang教授,從古至今,漢學的研究從未停止過。隻是在一開始,荷蘭開始漢學研究是出于控制殖民地華人的需要,所以“漢學”也成為了具有殖民色彩的符号。柯雷教授對此解釋道,不是以現在的傲慢責怪先輩,無疑當時學術已成為殖民的一部分,但更多的是大時代背景下的無奈。從客觀上來講,殖民主義着實促進了漢學研究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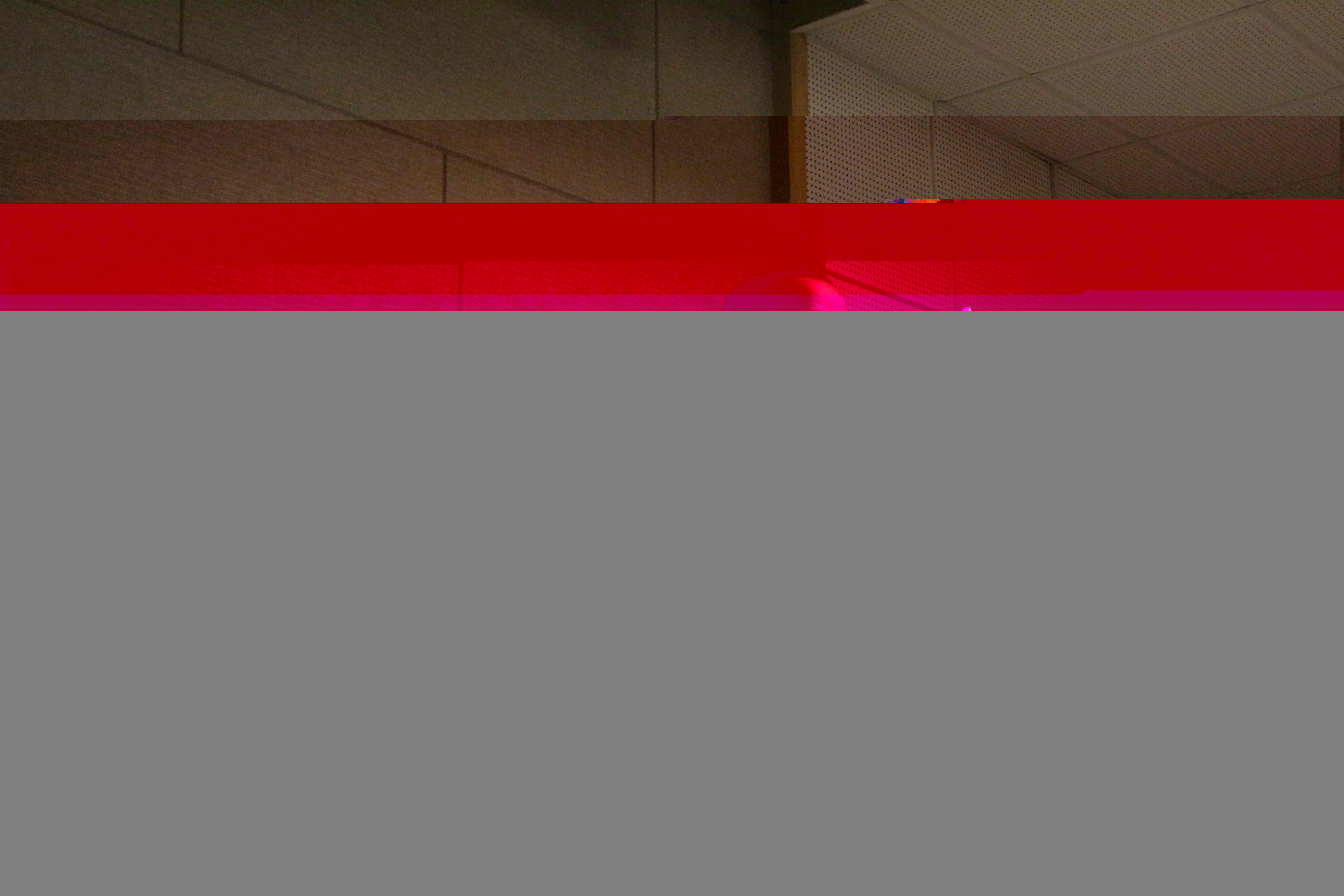
柯雷的“不可能”其實是為了闡釋在外國學者對漢學研究過程中面臨的挑戰,以及種種使得漢學可能中斷的問題。柯雷教授由三個方面論述了這個問題。第一即對于disciplines的定義以及區域研究,與大家讨論究竟“漢學”能否被稱為一個學科。如果隻是從傳統的定義即“學科的範圍”“自己的方法”以及“理論”看,“漢學”并不能被稱作一個學科,因為首先“漢學”所研究的内容是十分寬泛的,涉及人類學、宗教、曆史等多方面,而且處在文化研究全球化、跨學科時代背景下,難以确定确切的邊界,所以僅以此作為‘“漢學”不是一門學科’的例證顯然是不可行的。第二是關于Area Studies即區域研究的讨論,對于世界的三個不同時代來講,“漢學”的研究都有着不同的背景,柯雷教授認為世界的三個時代應該是“殖民地時代”“冷戰時代”以及“後殖民地時代”。殖民地時代以及冷戰時代的“漢學”研究都帶有很強的目的性,“漢學”研究對外國而言也是“了解他人繼而了解自己”的最好方式。但是後殖民地時代,是一個去殖民地化的過程,人們尊重區别,更加明确“本位”觀念,之前因為西方文化中的英語占據主導地位而緻使漢語成為田野語言的狀況已有很大改觀,學者們逐漸了解到,“漢學”研究不僅是學習語言,不是僅僅提供學習資料,更是真正了解文化。第三即是Translation過程中所要面對的問題,“翻譯”本意是将某物從某處帶到他處,實際應該是對語言的翻譯,對于culture translation 來講,對于文字内涵的理解愈發重要,柯雷教授借用了“暴風雨”這個詞語的例子,強調漢學研究過程中對于不同時代特殊詞語含義的把握。接下來柯雷教授就這一點介紹了萊頓大學近年來在漢學研究方面的發展,從漢學教授席到藏書四十餘萬冊的漢學圖書館的建立,學術研究群體的不斷壯大,都在體現着漢學研究的“可能性”。

在講座的最後,柯雷教授總結了現在漢學研究過程中真正存在的不可能。第一是“通”,每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是複雜而深厚的,即使是作為漢文化“局内人”的我們也不可能真正通達;第二就是漢學的“專利”,不應當作為一個漢學獨有的研究領域,而是各專業都應學習了解的科目;第三就是“封閉”,不可以不交流不溝通,漢學研究應該是全球化的。
在與在場同學的互動過程中,柯雷教授就翻譯誤讀以及區域研究中存在不同學科地位不同的問題分享了自己的看法,誤讀是在實踐過程中不斷修正的,而作為研究學者,正是在研究過程中讓他人了解自己工作的複雜性,尋求合作,證明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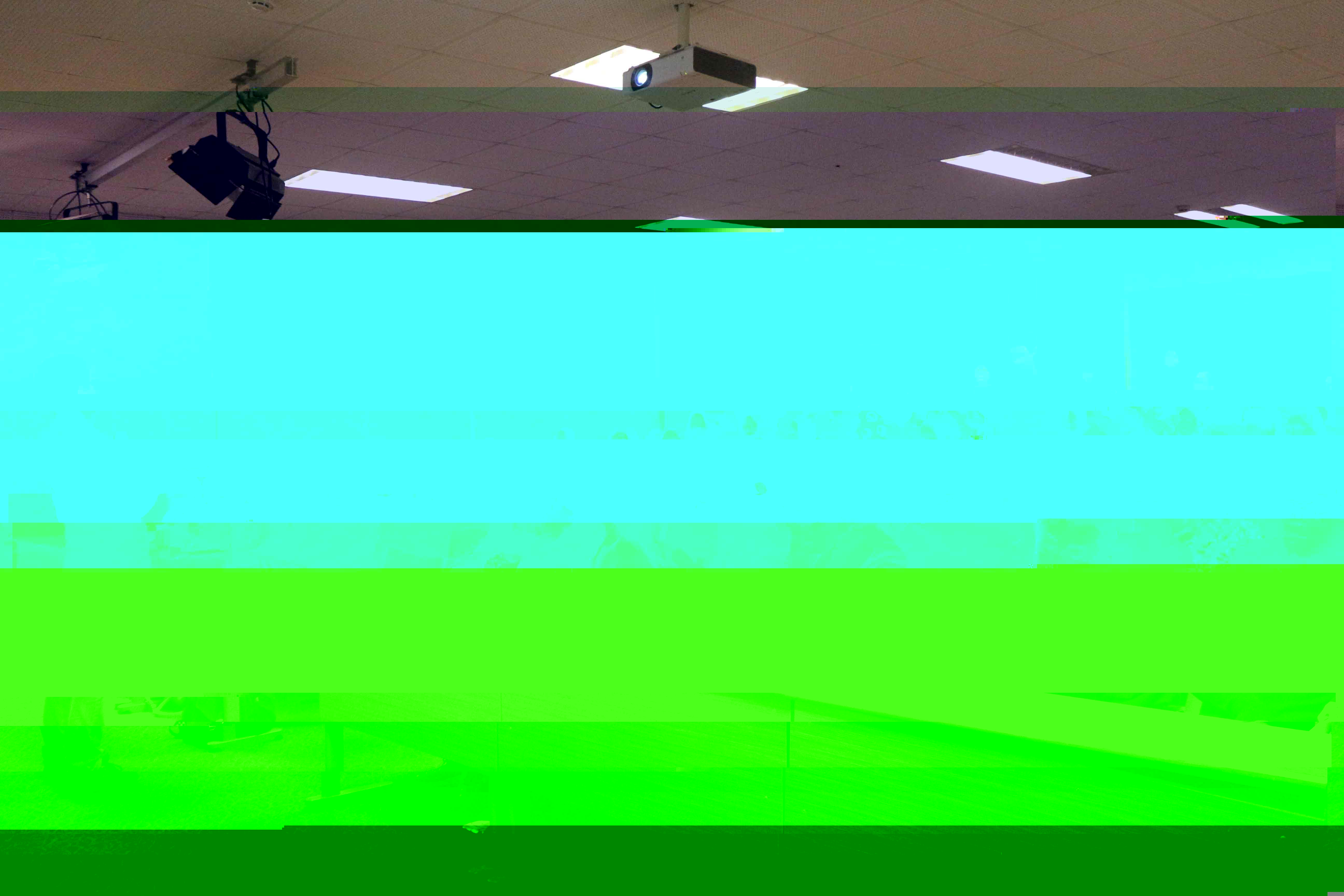
講座進入尾聲,筆者對于漢學也有了更多的不同層面的認識,不僅是因為柯雷教授那一口流利的中文所帶來的感染力,更是因為一種深深的自我認同感。漢學研究任重而道遠,柯雷教授的講演無疑為我們開啟了一個新的來自于“局内人”的視角。
文字 王雅喆
圖片 黃赟涵
審核 富俊玲

